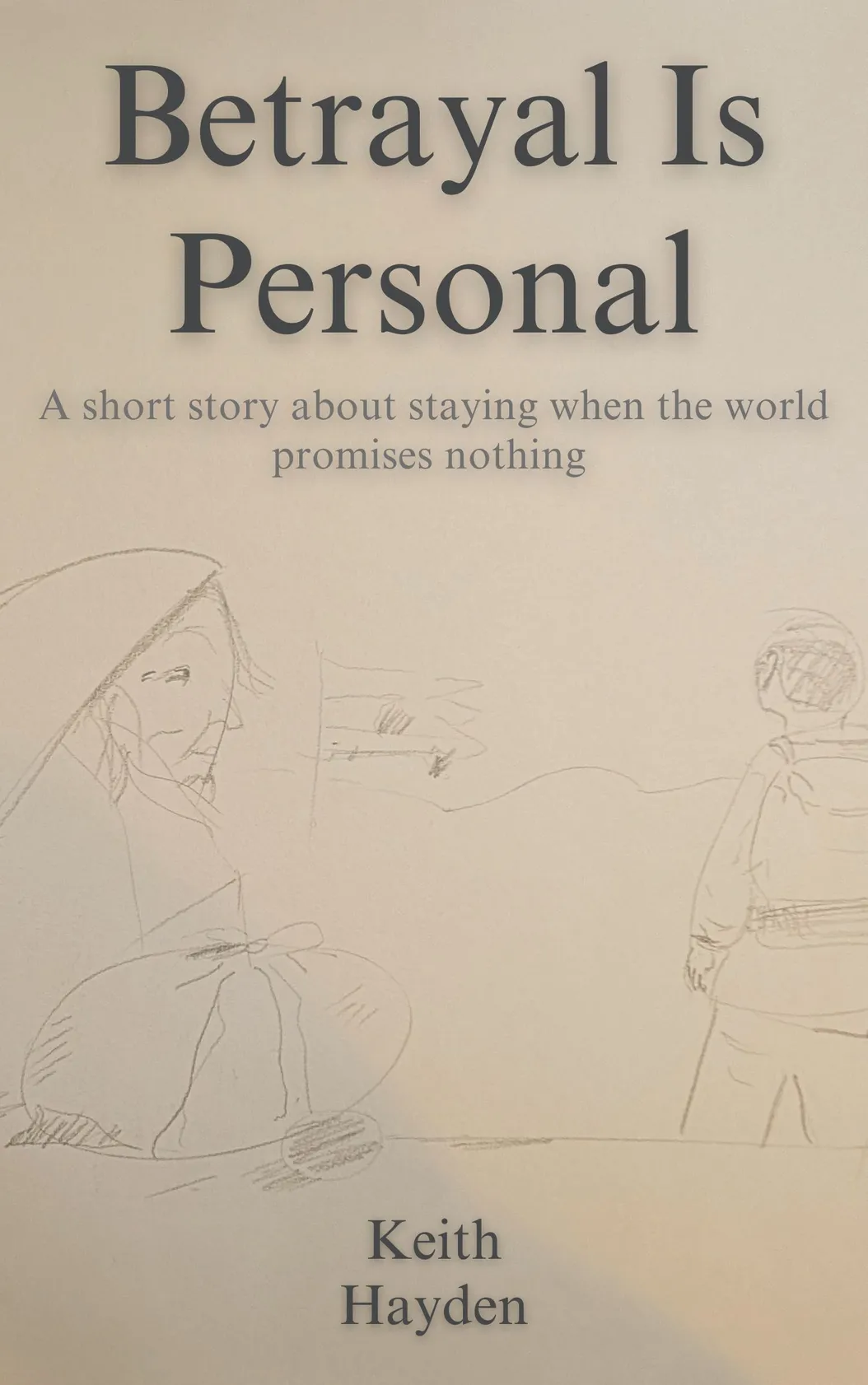“This depression has left me empty as a discarded can on the road.”
“Why don’t you fill it and pick it up then?” He tried to cheer me up as the dust rolled by.
“Because there’s no map through it. It’s a valley I can’t cross.”
“oh.”
We walked together with burlap sacks. Mine was torn at the corner. Some ambitious mouse did the job. A real Jerry with no Tom to chase him away.
His was newer and heavier. Poverty teaches boys how to carry weight. I taught him how not to expect relief. That’s what he calls my betrayal now. I call it honesty, though I’ve lived long enough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lurs.
Blood thins, roads don’t; only the space we travel does. That’s why he’s with me, he’s a possibility expander. As we walked among the dull golden dust, I blotted out the argument with my knees to study the trees. A Brant’s oak (Quercus brantii) stares back.
I thought: trees don’t promise fairness or shade, they grow because it is nature. The nature of people is too complex for me now. The modern world abandoned me like so many other elderly. I don’t see our destination any different, but I keep moving anyway.
“Stop,” he said. “Listen.”
“What is it?”
He put his phone out, the soft dome of light in the dark was a comfort. Through low quality sound, news of the Iran protests hissed through the static. It was a sister, a fellow wise woman shouting about how she’d already been dead for decades.
“Can she say that? Sounds like betrayal.” He said with youthful concern.
“Betrayal? No, betrayal is personal. This is impersonal. Governments deal with policy, not single people. They use power as if it were a weather system; most times you can ignore it, sometimes it wipes you out with a single signed sentence.”
“Sounds like my ex-girlfriend.”
That got a hard laugh out of me. He shut it off and we kept walking.
Morning rose up and we met others at the bottom in the streets. We shared bread, bad jokes, oranges passed hand to hand. The ground didn’t care who we were. That helped.
We sat on a curb as the sun climbed and the crowd grew. Banners, bloodied faces with determined expressions rallied around.
He asked, “Do you still think this will mean anything? That you choosing this honor will change the nation?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to make it as Allah intended?”
“The world doesn’t make guarantees. I don’t either. But we’re both here so…”
I clenched his rough hand. He lowered his head so I couldn’t see the emotion pull from him. I was fine with that.
Because we finally did it— we stayed together despite. Change was coming.
中文
“这场低谷把我掏空了,像路边被丢弃的易拉罐。”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捡起来,装点东西?”尘土翻滚着,他试着逗我开心。
“因为这里没有地图。这是一条我过不去的山谷。”
“哦。”
我们一起走着,背着粗麻布袋。我的袋子角落破了——一只野心勃勃的老鼠干的好事。活脱脱一个没有汤姆追赶的杰瑞。
他的袋子更新,也更沉。贫穷会教会男孩如何承重。我教会他别指望解脱。现在他把这叫作我的背叛。我称之为诚实,尽管活得够久就会知道,两者的界线会变得模糊。
血缘会变淡,道路不会;真正改变的只有我们走过的空间。这就是他和我一起走的原因——他是可能性的放大器。走在暗淡的金色尘土中,我让膝盖的疼痛盖过争执,转而去看树。一棵布朗特栎(Quercus brantii)正回望着我。
我想:树不会承诺公平,也不会承诺荫凉,它们只是因为自然如此而生长。人的本性如今对我来说太复杂了。现代世界像抛弃许多老人那样抛弃了我。我看不出我们的终点有什么不同,但我还是继续往前走。
“停一下,”他说。“听。”
“听什么?”
他掏出手机,黑暗中那团柔和的光让我感到安心。劣质的音质里,关于伊朗抗议的新闻在电流声中嘶嘶作响。那是一个姐妹,一个同样睿智的女人,喊着自己早已死去几十年。
“她能这么说吗?听起来像是背叛。”他带着年轻人的焦虑问。
“背叛?不。背叛是个人的。这是非个人的。政府处理的是政策,不是个体。他们使用权力就像对待天气系统——大多数时候你可以忽略它,有时却会被一纸签署的判决彻底摧毁。”
“听起来像我前女友。”
这让我大笑出声。他关掉了手机,我们继续走。
清晨升起时,我们在街道尽头遇见了其他人。面包被分着吃,冷笑话四处飞,橘子在人们手中传递。土地不在乎我们是谁。这让我感到宽慰。
我们坐在路沿上,太阳越升越高,人群也越来越密。横幅、带血却坚定的脸庞,在我们周围汇聚。
他问我:“你还觉得这会有意义吗?你选择这种荣誉,会改变这个国家吗?会改变我们的关系,让它变成真主所期望的样子吗?”
“世界不做保证,”我说,“我也不做。但我们都在这里,所以……”
我紧紧握住他粗糙的手。他低下头,不让我看见情绪从他身上抽离。我对此并不介意。
因为我们终于做到了——尽管一切,我们还是留在了一起。
改变正在到来。
از
«این فرورفتگی مرا خالی کرده، مثل یک قوطی رهاشده کنار جاده.»
گفت: «خب چرا پرش نمیکنی و برش نمیداری؟»
گرد و خاک میغلتید و او سعی داشت حالم را بهتر کند.
گفتم: «چون هیچ نقشهای برای عبورش نیست. این درهایست که نمیتوانم از آن بگذرم.»
«اوه.»
با هم راه میرفتیم، با کیسههای کنفی. گوشهی کیسهی من پاره شده بود—کارِ یک موش جاهطلب. یک جریِ واقعی، بدون تامیای که دنبالش کند.
کیسهی او نوتر و سنگینتر بود. فقر به پسرها یاد میدهد چگونه بار تحمل کنند. من به او یاد دادم انتظار رهایی نداشته باشد. حالا اسمش را «خیانت» میگذارد. من میگویم صداقت است، هرچند آنقدر عمر کردهام که بدانم مرز میانشان محو میشود.
خون کمرنگ میشود، جاده نه؛ فقط فضایی که در آن حرکت میکنیم تغییر میکند. به همین خاطر با من است—او گسترشدهندهی امکانهاست. میان گردِ طلاییِ مات قدم میزدیم و من با درد زانوهایم بحث را خاموش کردم و به تماشای درختان پرداختم. یک بلوط برانت (Quercus brantii) به من خیره شده بود.
فکر کردم: درختها وعدهی عدالت یا سایه نمیدهند؛ آنها رشد میکنند چون طبیعتشان همین است. طبیعت انسانها حالا برایم بیش از حد پیچیده است. دنیای مدرن مرا، مثل بسیاری از سالمندان دیگر، رها کرده. مقصد را متفاوت نمیبینم، اما باز هم به حرکت ادامه میدهم.
گفت: «بایست. گوش بده.»
پرسیدم: «به چی؟»
گوشیاش را بیرون آورد؛ گنبدی نرم از نور در تاریکی آرامم کرد. از میان صدایی بیکیفیت، خبرِ اعتراضات ایران در خشخش امواج پیچید. صدای خواهری بود، زنی خردمند، که فریاد میزد دهههاست مرده است.
با نگرانیِ جوانانه گفت: «میتواند این را بگوید؟ شبیه خیانت نیست؟»
گفتم: «خیانت؟ نه. خیانت شخصی است. این غیرشخصی است. دولتها با سیاست سروکار دارند، نه با انسانهای منفرد. آنها با قدرت مثل یک سامانهی آبوهوایی رفتار میکنند—بیشتر وقتها میشود نادیدهاش گرفت، اما گاهی با یک جملهی امضاشده نابودت میکند.»
گفت: «شبیه دوستدختر سابقم است.»
این یکی خندهی محکمی از من گرفت. گوشی را خاموش کرد و به راه افتادیم.
صبح که بالا آمد، در پایینِ خیابانها به دیگران رسیدیم. نان را قسمت کردیم، جوکهای بد رد و بدل شد، پرتقالها دستبهدست گشت. زمین اهمیتی نمیداد که ما چه کسی هستیم. همین کمککننده بود.
روی جدول نشستیم؛ آفتاب بالا میرفت و جمعیت بیشتر میشد. پلاکاردها، صورتهای خونآلود با نگاههایی مصمم، اطرافمان جمع شده بودند.
پرسید: «هنوز فکر میکنی اینها معنی دارد؟ اینکه تو این شرافت را انتخاب کنی، کشور را عوض میکند؟ رابطهی ما را طوری تغییر میدهد که خدا خواسته؟»
گفتم: «دنیا تضمین نمیدهد. من هم نمیدهم. اما هر دو اینجاییم، پس…»
دست زبرش را محکم گرفتم. سرش را پایین انداخت تا نبینم احساسات چگونه از او بیرون کشیده میشود.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چون ما بالاخره انجامش دادیم—با وجود همهچیز، کنار هم ماندیم.
تغییر در راه بود.